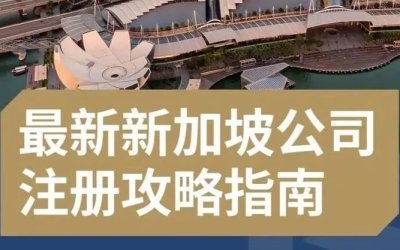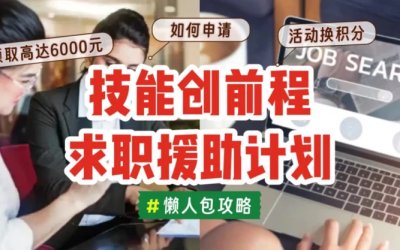新加坡,這個彈丸之地的職場江湖,最近可不太平,裁員潮的陰霾還未散盡,用人荒的焦灼已撲面而來。
人力部報告里那些跳動的數字,像極了職場溫度計上的水銀柱,忽地竄到了警戒線——職位空缺率創新高,連月薪過萬的職位都砸不出個水花,這齣"招工難"大戲唱得比新加坡河還要曲折。

"軟體工程師月薪13000新幣!"招聘廣告上的數字明晃晃地刺人眼,可企業HR的嘆息聲比鍵盤敲擊聲還密集。
在濱海灣金融區的玻璃大樓里,總監們望著空蕩蕩的工位直撓頭:"候選人簡歷收了一大摞,真正能扛活兒的鳳毛麟角。"

這看似誘人的薪資單,撕開來看卻滿是暗紋,就像烏節路奢侈品店標價牌上的零,總藏著不為人知的折扣密碼。
那位從馬來西亞飛來的應聘者,聽說要996工作制,轉身就買了返程機票;本地畢業生看著"3-5年經驗"的要求,默默收起了剛出爐的學位證書。
更別說某些崗位還要求"本科+專業認證+行業資源",活脫脫把職場門檻砌成了馬里安曼興都廟的台階。
最魔幻的是學前教育老師崗位,3700新幣的月薪聽著體面,可當應聘者聽說要哄哭鬧的孩子、處理家長投訴,還要應付教育部突擊檢查時,笑容瞬間凝固成濱海灣金沙酒店門前的雕塑。
這哪是教書育人,分明是十項全能的競技賽場。

在芽籠士乃巴剎的氤氳煙火氣里,清潔工阿姨正彎腰擦拭著沾滿油漬的瓷磚,她每月1740新幣的薪水,要養活遠在印尼的家人。
當僱主抱怨"本地人不願意做"時,可曾想過這份工錢是否抵得上周末被占用的家庭時光?那些在廚房後廚被熱油燙出水泡的助理們,看著2500新幣的月薪單,是否算過每小時的"燙傷補償費"?
建築工地的鋼筋水泥森林裡,工人們用安全帽下的汗水澆築著別人的夢想家園,可當他們看著900新幣的日薪,再摸摸口袋裡被中介抽走的"介紹費",不知作何感想。
更諷刺的是,某些僱主一邊喊著"用工荒",一邊在休息室里安裝著監控攝像頭——連喝水的時間都要精確到秒。
人力部調查顯示,近八成僱主鬆口說:"學歷嘛,差不多就行,關鍵看本事。"這種180度大轉彎,活像聖淘沙環島纜車在空中折返。
某製造業老闆掏心窩子的表示:"以前覺得本科生好使,結果發現經驗比文憑值錢。"他舉了個例子:廠里新招的技師雖然只有高職學歷,但調設備精度比工程師還快,這讓我想起牛車水老攤主的話:"挑荔枝要看果肉,不是看果皮。"

當增加法定年假的提議浮出水面,金靴商業區的會議室里頓時炸開了鍋,僱主們掰著手指頭算帳:多放一天假,生產線就要停擺,客戶訂單怎麼辦?可員工們卻在茶水間竊竊私語:連泰國勞工都有10天年假,新加坡人難道活該做鐵打的駱駝?
人力部長的表態像極了一道平衡木動作:"既要保護員工權益,又要給企業留活路。"
這讓我想起濱海灣花園的雙螺旋橋,看似糾結的結構里藏著精妙的力學原理,只是不知道,當最低年假從7天漲到12天的提案落地時,會有多少中小企業主夜半驚醒,數著天花板算成本?
新加坡政府放寬外籍勞工年齡到63歲的政策,在淡濱尼工業園引起熱議。
本地工友們看著柬埔寨來的新同事,心裡五味雜陳,一方面,他們理解企業開動機器的需要;另一方面,又擔心自己變成"溫水裡的青蛙"。
更耐人尋味的是,連廚師、重型司機都納入客工清單,這讓我想起烏節路美食街的場景:中國城的川菜師傅和印度裔的羅惹攤主,用各自的語言交流著炒鍋的溫度。
未來,當更多外國面孔出現在新加坡職場,本地勞動者該如何守住自己的飯碗?
站在2025年的時間節點回望,新加坡的用人荒不過是老齡化危機的序章。
當銀髮族擠滿組屋區的健身角,年輕勞動力的缺口就像濱海堤壩的裂縫,越來越大,企業主們今天為招不到人焦慮,明天可能要為留不住人發愁。

上周在人力部舉辦的研討會上,有位學者的話讓我脊背發涼:"未來十年,我們不是在和鄰國搶人才,而是在和時間賽跑。"這句話像樟宜機場夜空中掠過的飛機尾燈,閃爍著警示的紅光。
走在燈火通明的濱海灣,看著寫字樓里加班的身影,突然想起克拉碼頭那些繫著紅領巾的學童,他們清澈的眼睛裡,映照著新加坡未來的職場圖景。
當今天的職位空缺變成明天的崗位冗餘,我們該用怎樣的智慧,在人口結構的峽谷間架起通途?
這場職場大戲,沒有現成的劇本,每個參與者都在即興創作,政府、企業、員工,就像牛車水三輪車上的三個輪子,缺了哪個都會翻車,或許正如聖安德烈教堂的彩窗,只有讓光線從不同角度穿透,才能映出完整的彩虹。